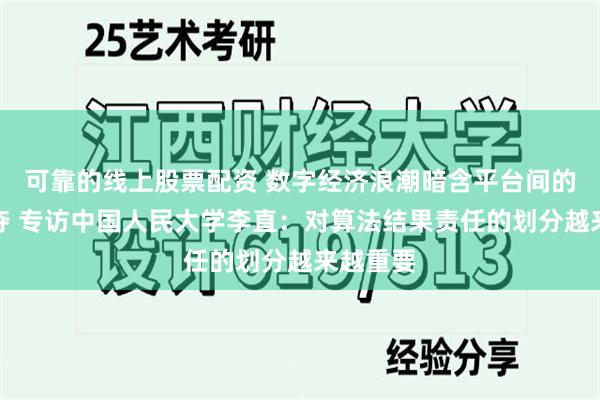
数字技术正在带来新的垄断与剥削吗?可靠的线上股票配资
从被算法“投喂”的短视频用户,到“困在系统里”的骑手,数字技术发展中的一些消极面正引起更广泛而深刻的讨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在其著作《技术封建主义》中,系统阐释了隐蔽在数字经济浪潮下的那些负面特征。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技术封建主义》一经面世便登上豆瓣商业经营图书热门榜前列。
什么是“技术封建主义”?这并不是说数字技术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倒退,迪朗认为“技术封建主义”是一种假说。这一名词的含义是数字技术正在让社会的运行重现封建社会的一些特征,包括封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租金逻辑以及封建领主实施的超经济的强制。在迪朗看来,网络空间正在成为新的“领土”,算法治理通过各种概率预测,剥夺了主体挑战现实的能力。
那么,一些“技术封建主义”的特征在我国是否存在?这种情况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哪些启发?围绕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近日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李直进行了对话。
李直提出,“技术封建主义”揭示了一些数字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特征,例如算法控制中的超经济强制、平台的租金转移机制以及平台对社会互动的控制,要更好地引领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正确地把握“技术封建主义”的特征。
算法控制中的超经济强制
我们已经可以从一些案例中捕捉到“技术封建主义”生长的痕迹。例如,骑手在平台算法影响下的困境,社交媒体用户会陷入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不同功能平台之间的高度隔离,互联网巨头对“资源”的激烈争夺……
李直提出,“技术封建主义”带有一定的一般性,互联网巨头采取的一些行为也在“塑造”着“技术封建主义”。不过,“技术封建主义”不是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简单否定,而是对数字经济运行特征的描述,更好地引领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正确把握“技术封建主义”的特征。
NBD:互联网平台的哪些行为构成了“技术封建主义”的基础?
李直:我国平台的发展也在塑造“技术封建主义”。这不仅是平台和数字资本具体的竞争策略选择的结果,更是平台技术运行架构特征的结果。
第一,平台的许多形式正在重塑封闭的“封建领地”的逻辑。平台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就像封建领地一样具有明确的边界,导致不同功能的平台之间的高度隔离。例如利用搜索引擎和浏览器已经无法搜索和浏览小红书和知乎这些内容平台的具体内容。
第二,平台的算法控制逻辑形成了平台对用户的超经济强制。平台运行的核心是以用户的数据为基础,不断地对用户在平台上的活动进行优化与即时的控制。尽管平台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性,但是却又限定了用户能够进行的选择。
第三,平台正在通过网络外部性提高用户退出平台“封建领地”的成本。例如随着一个人同所有熟人的沟通和工作安排都是通过某个App进行,那么选择不使用这个App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这最终会“强迫”一个人去使用这一App。
第四,平台正在扩展租金的逻辑。最常见的租金就是因使用平台基础设施而支付的费用,例如使用云计算和云存储能力的付费,以及平台从商品和服务中的抽成。其次,还有用户向平台支付的大量广告费用,包括为了让商品可以在搜索结果中有更好的排位而给搜索引擎和在线购物平台支付的费用。传统的通过知识产权获得租金的方式也正在平台化,例如向知网支付的下载论文的费用。最后,软件的使用也在从一次性的买断制转向月/年租制,其中的租金逻辑越发凸显。
NBD:因算法导致的“骑手困境”曾引发广泛讨论,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李直: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外卖骑手面临的“骑手困境”的问题既是“技术封建主义”的超经济强制特征的体现,也受到平台资本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而进行策略选择的影响。
算法控制是一个无人化的自动控制过程,这无疑增加了平台对外卖骑手的控制能力。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骑手越是为了符合送单要求,将送单时间控制在规定时间内,就越会导致新计算出的送单时间缩短,这就会导致骑手劳动强度增大、进行危险骑行等问题。但与此同时,骑手似乎也没有任何办法去对算法的结果进行反抗。
但还存在一个隐藏更深的问题,那就是谁来承担算法控制结果的责任。在现实中,平台更倾向于将算法塑造为完全客观独立的计算过程,而非平台获得收益的关键,进而规避了相关的责任。
2016年,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晋江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共同出资,通过与台湾联华电子技术合作,成立了DRAM内存制造企业福建省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简称“福建晋华”,具体运作方式为福建晋华出资,委托联华电子开发DRAM内存相关技术。
12月22日,特斯拉公司今天在上海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开展了拿地签约仪式,宣布了这一里程碑项目正式开启。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里谈到的算法结果的责任问题,因为随着我国社会智能化程度的提升,算法控制必然会成为越来越多领域的组织和控制原则,而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对算法结果责任的划分势必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例如近半年来,随着我国智能驾驶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开启智能驾驶后所引起的事故的责任,究竟应该由消费者还是厂商来承担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热点的话题。

图片来源:豆瓣截图
当平台操纵社会互动如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数字技术的马车仍在疾驰,数字经济的浪潮不会停歇。不过,“技术封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观察视角,引导数字技术更好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反垄断监管、出台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在李直看来,这些举措的确解决了消费者面对的一些问题,包括平台“杀熟”、平台二选一、算法过度利用成瘾性进行内容推送等。不过,李直也强调,在平台垄断和发展问题的背后,还要看到平台对“操纵社会互动”的巨大权力的掌握,进行系统性的政策构建。
NBD:在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中,如何平衡创新与反垄断、算法控制与用户权益之间的关系?
李直:只要接受了平台,就必须接受平台会控制社会互动这个现实,这是平台发展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社会权力结构性变化。换言之,只要接受平台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避免社会控制的权力向平台转移,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这种变化。而我国未来一定会朝着智能化社会的方向发展,平台的作用只会不断地得到巩固与加强。
所以,这里存在的一个更隐蔽的问题是,如果社会控制的权力越来越向私有化的平台集中,要如何防止私有资本对社会控制权力的滥用?
滥用平台控制社会互动的权力隐藏在很多平台垄断和发展问题的背后。归根结底,我们得根据不同功能的平台所掌握的具体社会权力来对它们进行合理的管制。
另外,平台可以依靠网络外部性、平台之间的互补性以及平台与硬件之间的相互搭配形成大规模的垄断。在租金逻辑的影响下,有可能对创新产生两方面影响:其一,平台只注重对可以获得更多租金和可以扩张垄断边界的技术进行投资;其二,平台获得太多租金可能会对其他人有负面影响,这类似于过高租金对实体商业中心和餐饮业的负面影响。
如果不能认识到平台的特殊性,纯粹从治理垄断的角度出发,并不能完全解决这里面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从平台垄断社会互动控制权力这个角度来进行系统性的政策构建。我国目前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就遵循了这个思路,也就是既要强调平台本身的发展,也要强调平台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才会提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一组概念。当然,这也符合我国政府一贯的政策导向,那就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设定政策的基础。
NBD:全球比较来看,您认为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有哪些特点?是否可成为其他国家的借鉴对象?
李直: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当然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意义,只是平台已经有了接近20年的发展历史,想要独立发展数字经济体系的困难程度在不断地增加。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有以下三个方面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第一,必须要坚持技术上的独立自主。独立的平台体系可以说是整个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目前全球只有中国和美国有比较完整的平台体系,所以也只有这两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展现出比较良好的发展态势。当然,美国平台的国际化做得更好,也对全球的数字经济有着更强的控制力。
2019年,仅仅依靠不允许华为手机安装谷歌套件,美国就扼杀了在欧洲具有不错发展势头的华为手机。
此外,欧洲近年来也在不断尝试从隐私和税收的角度限制美国平台的扩张,但是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政府必须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才能充分发挥平台的功能,并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与硅谷宣传的自由市场和企业家精神的乌托邦故事不同,互联网最初的发展就是为了满足美国军方的通信需求,所以说互联网本身就是非市场的、依托于国家创新体系的产物。而政府也一直在推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通信技术在2G到3G时代还相对落后,但是此后,政府一直在推动4G和5G网络以及光纤网络的建设。我国目前无论是网速还是网费的便宜程度都在全球名列前茅,更不用说政府支持的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大大提高了数字经济的覆盖率。
第三,最重要的还是政府要有能力,也要有魄力去制定发展政策,并遏制数字经济的不良发展趋势。我国目前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非常系统,既有支持平台自身发展的政策,也有考量如何充分利用平台功能的政策可靠的线上股票配资,还有促进技术薄弱环节突破的政策。此外,整个数字经济也被嵌入到更宏观的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政策体系中。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政府也采取了比较及时的监管手段。



